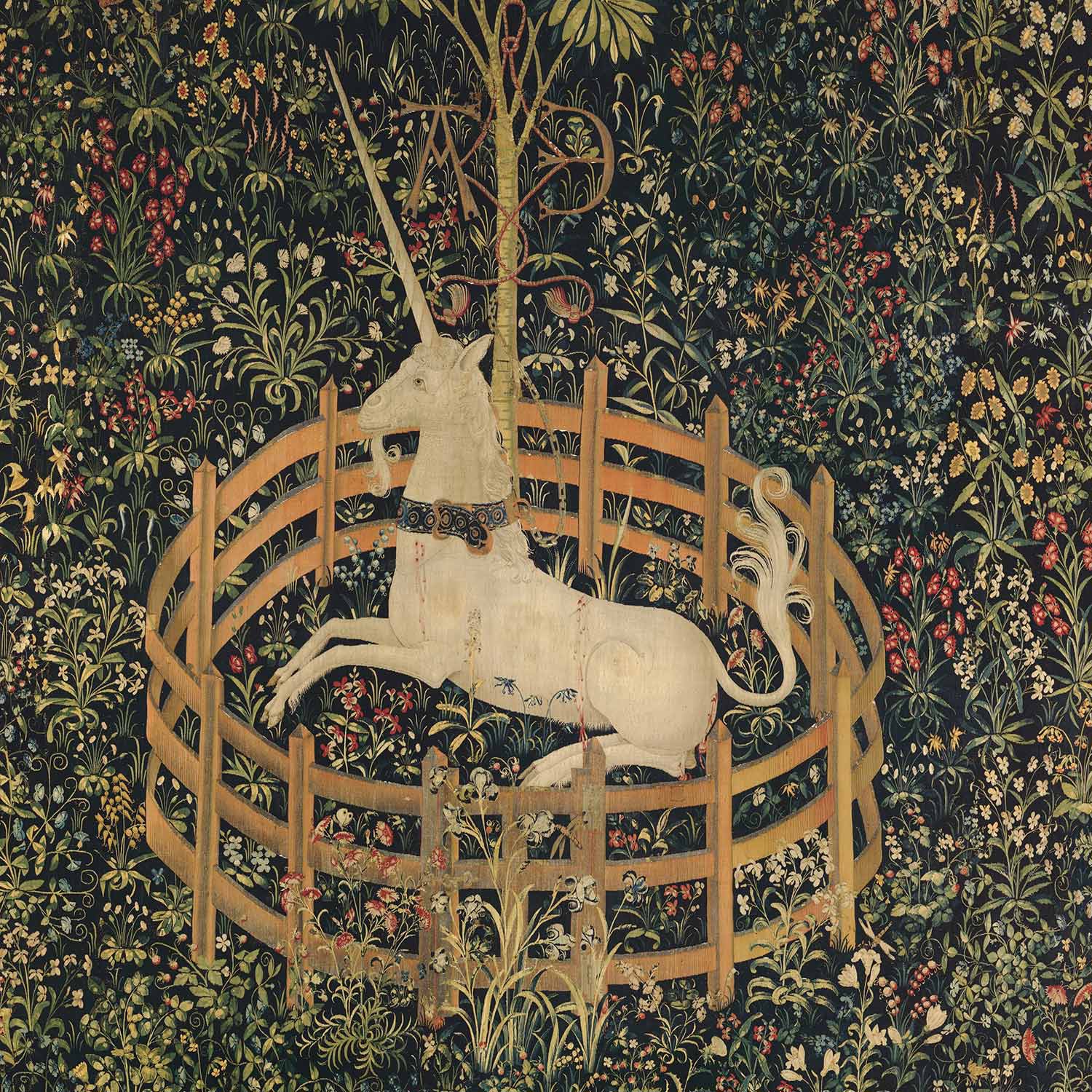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Apr 25, 2024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category
短篇小说
icon
password
这是城市被轰炸后的第二十三天,同时也是我在沙发上静止的第四天。我又再一次被震落的瓦砾唤醒。当太阳恰好移动到窗框残骸的一角时,外面的佯攻就会开始。游击队们午夜所埋下的炸药会在同一时间被引爆。那夜晚特有的遗世独立顿时烟消云散。我花费了大气力在藏匿在黑暗的微妙平衡,就这么被炽热的光线撕碎,露出毛茸茸的影子。身旁的一切都在运动着,循着时间以及演化的方向进行螺旋前进式的熵增运动。我却像顽固的粪石立在路中央,无视向东游行的队伍,执拗地躺在地面上。
今天的震动尤其猛烈,将我充满吗啡的身体都晃到在地,好像脑中的某个容器被摔破了、粘稠粉嫩的液体汩汩地挤压着心脏。大概是脑子出了问题吧,我紧贴着地毯的右耳好像听见了孩子的哭声。明明我那缺乏正常智力的孩子早就被送到了孤儿院中。我正想叫家里的婆娘把孩子带远一些,却被长年未见陌生感给敲醒了。妻子早就倒在了流亡的路上,只给我留下三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
或许是造化弄人,奶瓶居然从厨房的橱柜滚了出来。明明我躲在这里将近一个月了,却偏偏在我记忆复苏的时候将它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试图够到那个奶瓶,然后将它丢开。但沉重的身躯与其角力,布满臭气的地毯像是粘鼠板一样将我牢牢固定在原地。我想要抓这地板通过炽热的摩擦力前进,然而我破烂不堪的指甲就这么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可能脱落。看来我的身体很执拗,不能让我扮演爬行动物的角色。我将上半身撑起,手臂三头的肌肉里的吗啡不断沸腾,酸痛难耐。得靠着桌子的分量才能立起。
太阳从对面的楼背后逐渐升起,恰好照亮了正对着我的征兵布告牌。那位留着白色胡子戴着绿色贝雷帽的老人用右手手指指着我,左手腋下夹着的是锤子与镰刀。棕黑色的视线夹杂着不留情面的透视镜。能将一切不得体的藉口统统撕毁。有什么藉口能够比得上为国家的理念殉命来得崇高。然而这个老头施加给我的视线,早就被我身体生命力的缺失所割断了。在我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滑稽的老头。为了解放全人类!傻乎乎地在那叫唤着。外面那些青年游击队们就是因为厌倦了这些老生常谈的话才揭竿而起的吧。他们热爱的只有自私的新鲜感。
在医院被占领后,我就被要求去那些伤员们处理伤口。我很难将这些枪伤和这些青春的肉体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伤口浮游在肉体之上,在空气中飘荡着,只要抓着机会就会贴在干燥的肌肤上。在伤员中不乏女生的身影,她们裸露的肌肤是如此丑陋,红色的暴力纵深正在大腿外侧将青春靓丽统统卷走。残留的火药好似白色的蛆虫般蠕动在流动的肉身里面。在为她们缝针的时候,我试图将眼前的光景替换作妻子诱惑的大腿,然而她们杀猪般的叫声比任何恶毒的老年人都要难听。我强忍着喉咙的恶心感,如若表现出厌恶,抵在我腰间的步枪将会毫不留情地被扣下扳机。
倘若我的孩子还活着,大概与他们一般年纪。出于对父亲角色的失职也好,处于长辈的自大也好,趁着男生们不在的时候我壮起胆子向床上的女孩发问:开枪的感觉怎么样?
女孩布满汗珠的脸停下了颤抖,“你没有开过枪吗?”
我摇了摇头,表示没有。“我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女孩像是抓到了我的什么把柄一样痛快地笑了。“是嘛,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啊。开枪的感觉很痛快,就和你们男人打尿震一样,生理上整个人都会酥酥麻麻。不过,你不要试图动歪心思。你一碰到枪,他们就会给你打成筛子的。”
“放心,审时度势这种基本技能我还是有的。”我试探性地向前走了两步,确认对方没有警戒心后,我放心地坐在她的床前。“不过,我以为你们会有某些理想呢。为了情感,无论怎么样也不够说服力。”
“他们大概心里有数吧。我都说了,我什么也不懂。他们男人就爱说一堆听不懂的概念,什么超国民、三民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们既然能说出来这些东西,想必是明白当中的含义的吧。他们轻飘飘地将这些词语丢出来,感觉事情并不和我想象中那样困难。反正我没地方可去,为什么不跟着他们呢?人多好办事嘛。”
“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不幸福吗?我这句话是问你的,你不需要想象着非洲贫困地区的儿童把自己和他们作比较。请把你心里最直接的想法说出来吧。”
她眼睛变得迟钝了,蒙上了一段来自历史的阴霾,将她眼中的狂热与亢奋都截断了。“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当作没有听过。不过,非洲那边的孩子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也不清楚,地理上的距离让我对他们的认识只有贫困的代名词。因为生活的差距太大,我对他们很难有同情心,好像存在于小说一样。我也不是因为不幸福而挺身而出的。按照家里人的安排和帅气的公子哥儿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好……是啊,我一直都在拒绝……”
“那么是出于责任吗?”
“责任……我想不是。我和那些男人不同,他们的心中装着未来的国家、地球、人类的命运。我心里只装着我自己,我做这些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所有人都拿我们当还未开化的小孩,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幼稚的,高高在上地俯瞰着我们。那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只能进入你们规定好的世界,你们正是觉得我们无处可去了,才运用着高深莫测的理念支配着我们吧。说实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纳粹、军国主义,这些理念之间的演化关系我已经看得腻了。可我觉得很悲哀,这些某某主义能够自如地在同一片土地上互换、交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市民身上。而我们却还是只能在同一个粪坑里挣扎,更换领导的理念不过是换上了不同的香薰罢了。为什么就不能演化出适合大家的理念呢?对,帝国主义,这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敌人,所有的事情都能归咎于它身上。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变得更加高尚。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孩子。我不明白敌人究竟是什么,甚至自己的合理性也要逐渐不明白了。但枪火能点亮少许前面暗淡的未来,我很怕黑,怕得不得了,只有开枪我才能少许变得勇敢起来,盯着光线的尽头能暂时忘掉我自己悲惨的人生。”
身后的们倏地打开了,那些男孩子看到我离她坐得这么进,像是保护玩具不被玷污的孩子一样对我举起了枪。避开我的左右手恶狠狠地打了一顿,将我丢出了病房。
在之前的战争中我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的父亲则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而我面前的孩子们则是启动者。这类角色的演化是如此之快,几乎是放在几十年间,没有任何歇息的时间。也正因如此,这个国家当中的所有人都很难有“近代性的自我”。这些青年们也不例外,他们缺少适应演化的过程,历史的身躯早就被分割成断断续续的点,作为人类的连续性已经荡然无存。唯一从父辈传承的,只有古典的基因。对近代的追逐,和自然的身躯,两种冲突的属性碰撞在我们的体内,这才会令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如此痛苦吧。任何人都无法相互理解,简直是两个物种一样……不少人轻易地说出后现代这三个字,但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的是什么吗?这种无视石头过河的自大,任谁也会厌恶吧。
楼梯间有两个并排的窗框,中间的窗棂恰好将天空分割成一紫一红两片截然不同的光景。它们就像卡在喉管的血栓一样,给生活在这片天空下的所有人增添了几分赤痛的哭意。
一路到达体育馆中央,繁复的口号在半空中交杂,只能依稀听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将劣根性从我们这代阻断”“性解放即为自由的解放”“高鼻梁,低文明;金眼睛,势利眼”。
这些抽象的口号就这么在天上乱飞,不留痕迹地掠过人们的大脑。所谓新时代的个性阻断了我加入他们的渠道。我身上陈旧腐朽的肉体对他们唯一可取的只有外科医生的知识,若是将我从这个身份脱离出来,他们将会毫不留情地将我作为糟粕杀害。他们不为了纯粹的单个立场而行动,不为了诉求什么。如果硬要说的话,他们不过是热爱概念,痛恨现实的人罢了。被相同情感的秩序所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成为由各种各样的不满聚集而成的暴力的混沌。我对这些孩子没有受到正确的政治教导而哀伤。因为害怕社会力量的聚集而对孩子们采取了政治上的阉割。学校中的政治课程成了单薄的宣传手段,大概缺少直面的冲击,大家才会转而投向实用主义的怀抱,诉诸最直截了当的手段——暴力。
角落堆放着成群的枪械,像是受刑的柴火那样堆出尖锥的形状。那些男生和怀着孕的女孩们津津有味地在枪械构成的斜面上交媾着,甚至伸出舌头舔舐她们的下体。射精后男人们就会连滚带爬地离开女人,光着下半身围坐在一起,进行细致地研讨。好像交媾是成人的大门一样,若是不射精,男人永远是一个小孩。听着他们发出唰拉拉的动静,嗅着火药和汗液的味道,作为父亲角色的担忧而产生的情感超过了性欲。在这种情况下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么会健全。我仿佛看见她们怀着的,都是我那脑瘫的儿子。我不忍直视,可我无处可去,只能在肉团的腥臭味之间忍耐。
意料之外的重逢,我的儿子孤零零地站在门边,肩上挎着枪,歪斜的嘴角淌着口水,任何经过的青年都会敲一下他的脑袋。他那空洞洞的脑袋发出的声音沉闷极了,好像内里空空的。他似乎没有看见我,看见我的话估计也认不出我吧。他是个没有自我的人,不过是基因塑造而成的造物罢了。我这些年来不断在说服自己,将孩子弃离我身边是无比正确的决定,我孤身一人怎么可以将他抚养大呢?身体的残缺性着实令人胆颤,更可怕的是由身体的残缺性而导致的精神的残缺性。可以说,无论在哪个角度,他都不会是一个出现在这里的生物。
突入起来的空袭令性爱的欢愉轰然倒塌。男生们一下子穿起裤子冲了出去,我回过头,我的孩子已经不见了。我趁着四下无人,尽可能地将所有吗啡给带走。
再后来的事情,我和你们一样一无所知。
一块灰色的云遮挡在楼顶的上头,空气黛蓝的本色就这么落在我的头皮上。拖着腿,走下了残缺的楼梯,堂而皇之地走在大路的中央。本就是为了赴死,而路上除了死的寂静之外什么也没有。和我想象中炮火连天的阴霾大相径庭,我只能与微不足道的求死欲一同前行。
这段路比记忆中的还要柔软,光着脚却有瘙痒的感觉,像是踩在风干的毛豆腐一样。大概是战争后的焦土吧,我的脚已经认不出土地原本该有的质感是如何,因而也不知道焦土究竟有多厚,要用多久的时间才能清除。
我预期中的突然死亡还是没有出现,神迹发生般安然无恙趟过了战线。原野中,一座被风还是被什么刮倒的帐篷摊躺在视野的中央。那饱受雨水攻击的墨绿色之下,似乎还有一块黑色的生物,以微弱的动作蠕动着。我不自觉地朝着黑影走去,这泥泞的道路愈发坚实。那朦胧的黑边也变得具有实体。在那人形的角落,忽地闪了银色的光芒,被缓缓举到太阳穴的位置。我冲向前,将他手中的枪扭向地面,将弹夹给打空。
待到耳中的蜂鸣消退,我们毫无隔断地对视着。他的眼珠子布满了恐惧的血丝,染成了赤色的镜子。在我赤色的半透明影子之下,浓厚的陌生感在他的眼眶打转。不光是对面前的陌生人,也是对自己的陌生感。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还在寄希望于他人能够完成自己的夙愿。而当这份使命必须交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才发现指缝中还闪着渺茫的希望之光,无法轻易地将其舍弃。我摊开手,指缝的光芒变得更加灿烂,显得我那赴死的觉悟是如此幼稚。在这一刻,面前这稚嫩的躯体所蕴含的力量比我更加成熟,脸上刻满了不属于他这个世代的苦难。
他抓着我的衣襟,用质问的语气说道:“我会变得和你一样吗!你说!你说啊!请您立马说会吧!求求您了……”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不是针对会不会,而是针对“你”。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愿看见赤色的影子凝固。吗啡的作用已经消散了,我的胃部开始饿得发疼。我不愿我的身体活过来,可这个疑问不断地将我从安眠的土地里扯出。我的身躯开始对“死”产生了戒断反应,脑子不断地喊着,死吧!死吧!死吧!
“明明都是为了国家好不是吗?为什么要有分歧呢?我知道,这种话说出来会被说是天真,幼稚。可我的的确确是这么想的呀!谁也别说谁的理念更加好!所谓的主流不过是在某一段时间中暂时获得了胜利罢了!
“他们都在说自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只要不参加他们的运动就是与时代背道而驰。可如果没有了生命又谈何未来!我不希望……不……应该说反感!拒绝!抵抗!他们所构造的未来!但我没有能力抵抗,倘若诉诸暴力,不就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了吗!所以我只能,只能把枪口对准自己,说到底,我还是没有觉悟……”这孩子,湿润的眼眶柔化了眼中的愤懑,整个身体也顿时失去了气力窝倒在我的怀中。某些粘腻的情感涌进了我心里的缺口。将我往下沉了几厘米,陷进了像是女人一般温润的土地。“让我和你走下去吧。”
一阵剧烈地晃动,我感受到自己的掌心有刺痛感。心理的某些担忧从掌心的小孔中从我的体内流走。我拼命地睁开灌了铅的眼皮,一根长条状的红色针筒垂直地扎在我的掌心。在自我的红色的扭曲影子后面,还趴着一名皮肤松弛的年轻女士。啊,我这才想起来,原来我是一名和怀着孩子的女朋友睡在铁皮房屋中的二十三岁少年。将针筒内的内容物全部打入自己的身体,那对于未来的担忧又再一次消散了。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1df77c82-d783-4fca-b1d9-ce7d55576d47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