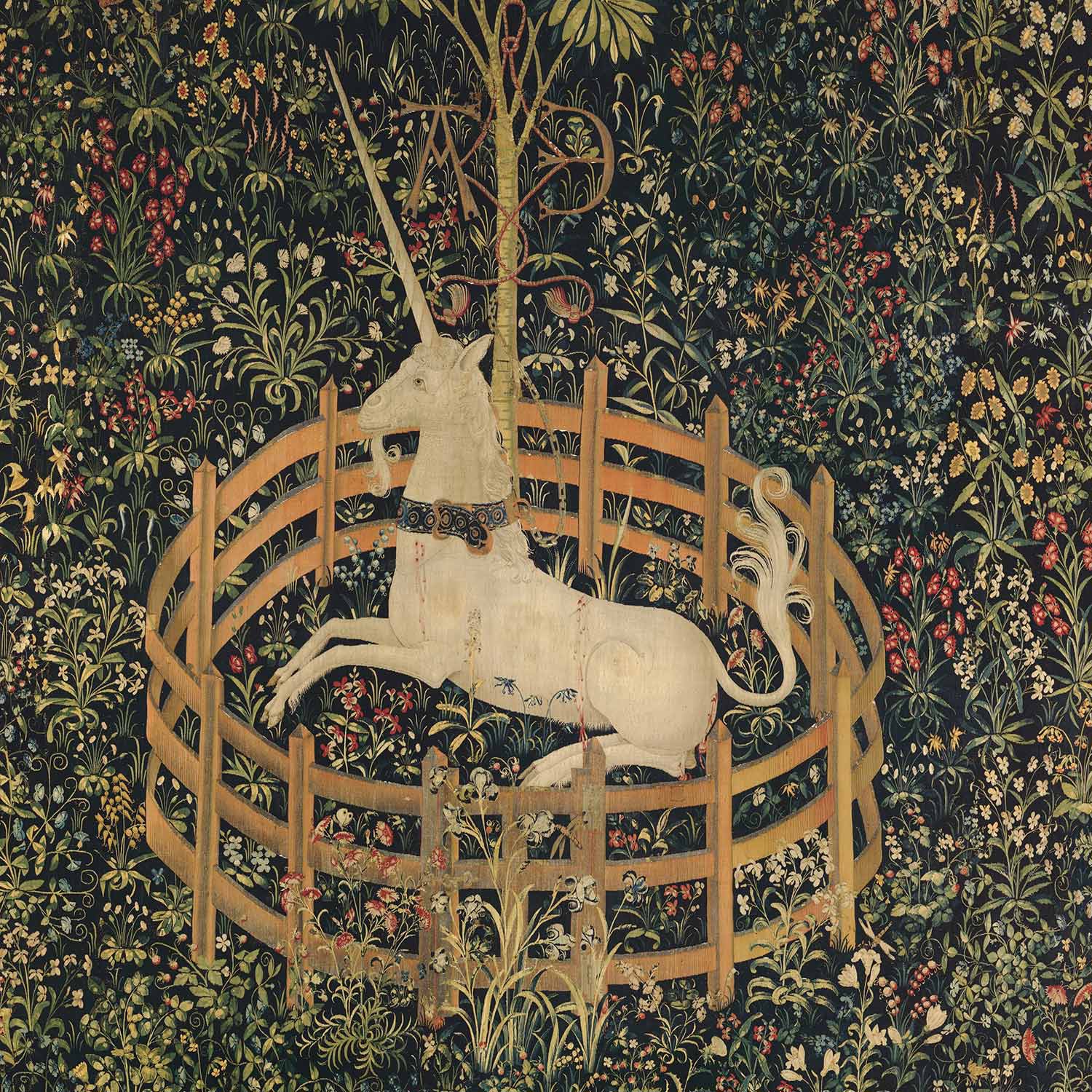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May 22, 2024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category
短篇小说
icon
password
人人说我傻。
我知道有首歌这么唱,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我也不例外。傻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很多人看到傻子都会笑。我听见傻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也会笑。我很开心傻的是我,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被笑。
在生物课上,老师讲过,近亲结婚的产物很大机会得遗传病,出生的孩子大多缺胳膊少腿,或是少了一只眼睛,相比较之下智力缺陷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智力缺陷是幸运的,不过老师这么说,我听起来也很开心。
在上这一单元的时候,我的名字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吧。只要一谈起“变异”、“唐氏”,好像它们是我名字的代名词一样,齐刷刷地将目光放在我的身上。我的心里也会有些不安,几乎要主动跑到台上扮演一只猴子,来解放他们的好奇心。 实际上我不喜欢猴子,可以说这世界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因为他们长得像人,我很难将他们当作是野兽。我不愿意看到这世上有比我更愚蠢的人。蠢于我是一件乐事,但于别人就不一定了。我欣然地接受了自己蠢这一事实,可为什么还有人要遭受这一名号呢?曾有人被指名道姓地比作我,立马气得将对方耳朵咬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有种愧疚的感觉。原来傻人哪怕什么都不干,只要活着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冷淡极了,可我不是因为对方被报复而沾沾自喜,只是单纯地有些绝望罢了。
下了课后,他们像是一群猴子一样好奇地望着毛发稀少的人类,对我发出种种疑问:你的爸爸妈妈是兄妹吗?还是说你是爸爸和你姐姐一起生的?也有可能是你和你母亲生下了你自己?在这社会上我知道有一种好奇心,是“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这种好奇心不好,电视上一般有这种心理的角色都没有好下场。可我的同学们问的是“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来的”。和电视中的截然相反。既然那是不好的,那这就是好的。我非常高兴大家对我产生了好的兴趣。
回到家后,我问爸妈他们是不是兄妹,他们只是淡淡地否认了这个事实,好像这个问题是跨过路上必经的水潭一样。也有可能他们活得已经够久,久得能够预知我问的这些问题。接着我问,我生出来的孩子也会变傻吗?
“你找得到愿意和你结婚的再说吧。”
“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孩子吗?”
“不然呢?不结婚就生,生出来万一和你一样有什么问题人家就跑了。”
“结婚就会一直在一起吗?”
“是吧。”爸爸手上的掌机不断发出金属的碰撞声,听起来就像是爪子划着金属片一样。
“那爸爸你和妈妈离婚吧,我要和妈妈结婚。”
“结你个死人头。”爸爸把手里的游戏机丢在一边,光着膀子进了厕所。
爸爸就是这样,每当谈起事情来,只要说不够两句就会躲在厕所里。某次拿着31分的语文试卷给妈妈签名时,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躲在厕所里。不过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堆积在水箱角落的尿渍散发着腥臭味,门外母亲也依然在哭诉着补习班的钱打了水漂。我依旧无法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安全感——或许因为这不是我的尿液。只有像狗一样的动物,才会用尿液圈地。随着磨砂门后的人影消失以及响亮的摔门声,爸爸站在门前叫我出去。
“我不想去补习班了。”我说。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在厕所里?”
“人总会有三急的,管这么多。一天十多个小时我都要和ta对着,见到ta我都嫌烦,有些时候我还情愿多呆一会儿。”
“我是说没有水声的那几次。”
“平时不见你这么聪明。”玻璃后的爸爸把报纸卷在一起,挠了挠背后,“要是你说的真的有用我也不会躲在厕所,ta少说两句就当帮忙了。婚也离不成,离职也离不了。”爸爸把电话挂掉,用报纸朝着门挥击,“喂,再不出来,我就让妈妈回来打你。”
和前文说的一样,我有一个姐姐。不过姐姐不是我和妈妈生的,是爸爸和妈妈在我出生十年前生的。不过我们很少见面。不是因为关系疏远,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读初中了,等到我读小学,她就已经去高中住宿。等到我有自理能力住在学校里面,她就已经嫁人不在家里住了。所以,相较说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是记忆,更多是有想象成分的谎言。
所以对我和姐姐一起生活的假期,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哪怕是一丝能够作为提示的事情都没有。如今姐姐已经搬了出去,流产了两次终于生下一个小孩,我也从大学毕业了,学生时期的回忆已经没有任何缝补的可能。
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独生子女,我也不自觉地代入了独生子女的家庭属性中。这几乎是一种共识,类似“到西方旅游(留学)是身份的象征”一样。只不过这种转变更加迅速,而且不依赖着某些实体、精神象征,在人类身上看不见任何连续性。这种沟壑在代际上也被抛在脑后,仿佛成了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被人类所淡淡地接受了。
我想,所有少年在这一情景下都是一样的。像是被邀请到一档具有政治倾向的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我们自然会不带丝毫羞愧和焦虑说出符合要求的话语。在温润的眼眸子底下,所谓的坦诚与公正大多会变成别人眼中扭曲的倒影,真正的自我只会陷入可言却不可即的尴尬境况。在当时我自以为能够轻松地融入了环境之中,但现在想来,所谓的融入大概不存在吧。毕竟所有人都在考虑自己呀,甚至我成了最为他人着想的一个人了。如今我似乎能够平淡地接受了心中莫名的疏离感,毕竟我们身处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绕着疏离的个体让行的。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爸爸很生气地对着刚高中毕业的姐姐说。
“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妈生我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已啊!说白了你也是个变态!”
爸爸第一次扇了巴掌,姐姐脸上的掌印的颜色和父亲脸上的一模一样,好像某些人生道理经过血脉传到姐姐的脸上,她没有说什么,满脸写着无人理解的愤懑。直到七天后,她被男朋友家里赶了出来,才在她脸上看到另一种麻木的神情。
妈妈光着身子,在闷热的阳台洗着衣服。乳房如同垂死骆驼上干瘪的驼峰般在半空中相互撞着,眼睛被汗水腌得眯了起来。甩在地上的水滴被烫出蒸汽。她的声音一下从刚烈转为释怀,“这太正常了。”
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正常、变态指的是什么。漫漫人生路我所度过的日子似乎都不那么正常。我有一个姐姐,我有健全的家庭。这些都是特殊的事物。如果说正常的姊弟关系是有血缘关系的、无可不谈的好友。从这方面来看也是毫无正常性可言的。我唯一能够思考得出的答案,只有代际之间无可缝补的鸿沟。
爸爸知道姐姐流产后,嘴角翘出了意味深长的角度。我确信,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因为当时除了爸爸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忙着疏解母女二人的哀伤。我无法融入,好像舞台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所有健壮者都在山上抱团取暖,而我和父亲则被留在谷底,永远也无法企及。面前的景色几乎是无可救药的绝望,我的心情也是死一般的冷淡。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孩子的死而伤心,好像他们认定了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是健全的,能够让家庭、社会存续,丝毫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想起学校广播中副校长说的那段话:最近不断有学生在自杀,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个道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怀胎十月不是让你们寻死的。你们是你们母亲的孩子,接着才是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别令人不省心。
明明今天应该是开心的,如今却落得这个田地,我开始对素未谋面的婴儿产生了憎恨,把我的美好的一天都破坏了。但诅咒人去死,已经是我能够想到的最狠心的话了,对于死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惩罚他们的办法。死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我死后会是怎么样呢?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宴厅中的哭啼声,我跑到舞台上,给麦克风通上电,把麦架调到合适的高度,回想着幼儿园的教育,开始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唱不够两句,我便被撵了下来。爸爸只好笑着给他们谢罪。
后来(没记错的话,大概是98前后),爸爸学着他的同事,故意将手伸进机器里把无名指第二节弄断了,拿了一笔赔偿金。用完了之后又觉得不过瘾,把玩具厂的钱卷走了。在那之后,一直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妈妈也再也不能安心地当家庭主妇,又重新回到了劳动之中。爸爸留下的东西只有游戏机,我以为这会是他在厕所最重要的乐趣,去到哪里都会带着。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空间太多了,才导致我的误会呢?原来做亲人,只用有血缘关系就够了,根本不用相互理解。
个人想法什么的可能会说一下,但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绝口不提,却又不是爱聆听别人苦恼的树洞。无时无刻都处在私人的世界中,摆出一副无人能理解的幼稚姿态。爸爸大概就是这种形象。这种幼稚做派的人究竟适不适合当父亲,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大概也是有不少负面情绪的,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自己可能也不以为意,暂时性地忘记就以为是康复了。毕竟生活上的事情要追求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要这么天天盯着细枝末节过日子眼界会变得狭隘的。
既然我能这么轻松地总结出来,我想我某一部分也和他相似。情绪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涌上来,那种窒息感是无与伦比的,像海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只给你最低限度的喘息时间,在你还没反应过来该为什么而哭的时候另一个情绪又扇了你一巴掌。要说起来,我也是情绪上的傻瓜吧。
渐渐,妈妈也到了病痛缠身的年纪。长期做洗衣工接触化学物质已经让她的指甲发黑发黄,像是脓包一样饱胀起来。而双手的肌肤却像是烧伤过后一样光滑,在射灯下还有一定光泽。身上的这个部件对于一个中风病人来说或许太过于难以操作,所以我必须得每天过来给母亲喂食,擦身子。我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吗。他摇了摇头,跟我说除了大脑的毛病也还有心脏的毛病。两者的治疗方式刚好相冲突,能用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多大用处。“通波仔”,开颅,对现状都没有什么帮助。身体内部能堵的都堵光了,就跟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一样(他一说完这个比喻就露出说错话的表情)进退两难。
我学着护工的样子把妈妈翻了过来,把脸上的鼻涕和口水擦干净。剩下的场景那就不能随便跟别人说了。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妈妈现在和我小时候一样蠢,我蠢过,如果有人面对面跟我说我以前的事情,我大概会羞愧难当至生气吧。所以我也不想说太多妈妈的事情。
我在门外听到房间里面传出啜泣声。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见姐姐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掩着面。为了不打扰她,我决定在贩卖机旁喝着速溶咖啡。等到她像个没事人一样出来我再走上前去。
她顺势坐在墙边最外面的排凳上,见我没有反应,她又往里面挪进去一个位子,拍了拍椅子示意我坐下。
“其实我很羡慕你,有些时候也想过跟你交换,看看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怎么会在那个场合唱生日歌。”
“感觉我的世界很单纯吧。我也大概能理解。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开始觉得以前的自己太过于单调。渐渐不想想起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实际上真的换了过来,你大概率也不会变吧。”
“都是后话了。”她转动脖子时有发条上链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如果像以前这么给别人添乱下去,你应该会讨厌我吧。”
“这么说你以前不喜欢我咯。”
“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该如何讨厌一个人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就像踢走路边的罐头一样。”姐姐的皮肤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更加浮肿,像是在福尔马林泡了几个月的标本一样,唯独眼睛吐露出严肃的红色,“我觉得你太自由了。好像所有人都对你没有保有希望。明明你是男孩子啊。在中国男孩子就该挑起大梁。你却因为智力上的问题一直不被看好。我只好被当作备选方案临急临忙的被抚养大。这算什么。我什么都没得到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吗?也不清楚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以下这些话,已经是脱离了故事的范畴了。好像《麦兜故事》的最后一样,要站在海傍(或是某些心旷神怡的景色),说点升华的事情,用漂亮话掩盖一下苦闷。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正站在厕所中,望着格栅窗户看着黛蓝色的晚霞,数着一架架闪着红绿光的飞机。
说实话如果会让大家觉得我傻,我也无所谓的。我也知道就凭我这脑子大概也说不出什么警拔的道理。如此长的人生中我便是这么粗线条地过来的,相较于家庭、工作中的道德伦理,如何利用对方的消遣开解自己经已是独属自己一份的历世经验。
在妈妈病床边时,我没有把这些神秘的经历告诉给妈妈。因为我开始觉得傻并不好,会令我不开心,我不想变傻。这种心情应该是大家都有的,所以我想着,这些话这么普通,也还是不要说出去好了。姐姐也是一样,自从哭了之后,就开始不说自己的事情了,只是默默念着报纸。或许是不喜欢谈论自己,也或许是自己的生活已经一一告诉殆尽,只能靠别人的生活维持住母女之间仅剩的体面。
虽然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之前姐姐和她说了什么,当中有没有我已经忘掉的记忆。我不清楚遗忘是不是长大的象征,不过站在当下的我重新回看自己,才发现本来当作日常的生活原来是这么特殊。除了我的蠢,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什么缺陷。而我同学们大多是离异家庭,要么失去爸爸,要么失去妈妈,好像他们都是乱伦的产物一样缺胳膊少腿。然而同学们却比我健全,这个健全却没有成为维系家庭的枢纽。
而我们家呢?爸爸离了家后好像跑路到越南去了。在妈妈病倒、我懂事后他又再回来了。姐姐也是一样,带着孩子一同回到家中。我的愚蠢治好了之后好像家里的缺陷也被缝补好了。我开始能够明白老师口中的“幸运”是什么了。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