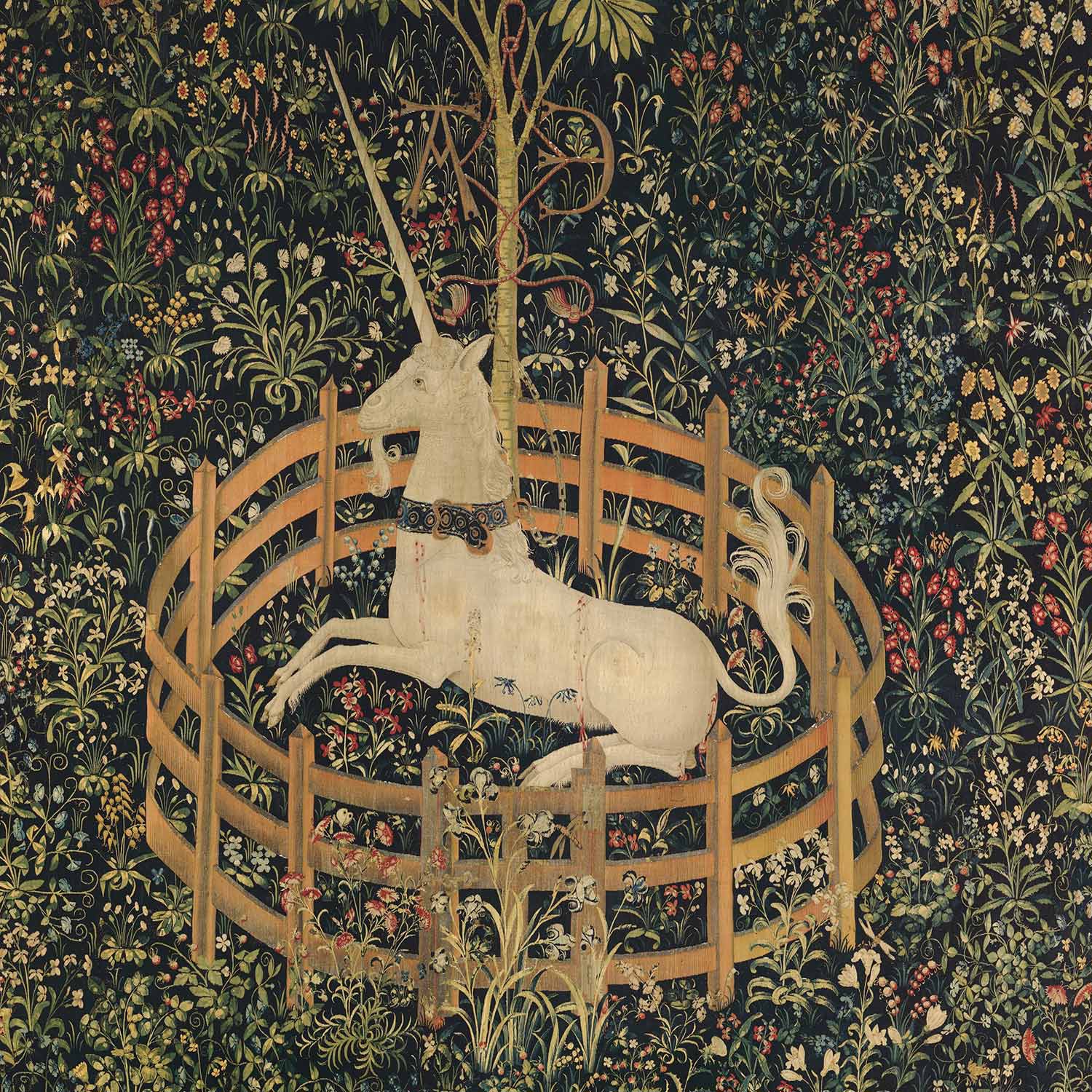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Sep 3, 2024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category
短篇小说
icon
password
七月一日 星期一 天气晴 爽朗
电线杆正在从马路旁的方向一点一点开始消失,除了我之外察觉到的大概只有拆迁的工人了吧。这一转变好似具有侵蚀性的化学反应发生在这座城镇之中,缓慢地、克制地、丝毫不想让人发现地默默发生着。日落的太阳紧贴着电线了,如果你孤独,你可以转过身去,和太阳来一场“木头人”,读好秒数,转过身去,你就会发现看似静止的太阳向下沉了几分。这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游戏,因为这是时间的游戏,而时间是不讲道理的。所以长大后我没有心思去和它玩这种不公平的游戏,我就只是默默看着,看得出神。
望着电线,直到落在线上的太阳变得模糊,周遭变得毛茸茸,摸上去会有痒痒的感觉,踩上去会有沙子藏在趾缝中感觉。那就对了,保持住这一感觉,将视线的焦点放在线上,而注意力放在太阳上。在精神和意识的差序中,你会慢慢看见太阳消失了,它的边界被破坏了,颜色溢出到你的眼眸上,把你所见的一切都变成金灿灿的。其实,这是有些悲凉的场景,你的意识就这么被黑暗吞噬了——和阳光一起。周围的一切朝着视线的边缘坍塌、萎缩,几乎要把你的灵魂吸干。我沉迷这种感觉,能从中感受到等待的愉悦,而不是孤独。
如果你问我:我在等什么、看什么、期待什么,我回答不了你。人生总有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又或者说,意义本身微小到无法被察觉,只能算是诡妙含蓄的缘分,最终在暮年总结人生的时候换来一句:啊,原来是这样啊。它既可以被解读成死亡的接近,希望的降临,生命的轮回,只要你需要,简单的电线杆中什么都有。真的,什么都有,取巧地把生命的意义交给它也不为过。电线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它从一个屋子转到另一个屋子,城市之所以成为了城市,也多亏了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的纵深感。
在金光摇曳的世界里,真正活着的生灵只有你一个,确切地只有你一个,而死在你的世界的也只有你自己。你的灵魂能够独立于你的肉体默默地看着它消亡,仿佛看着一个落在石缝间的树叶从有形的鲜活个体变成腐败的细胞。是的,电线杆就是这种感觉。每座经过城市化的地区都有各自的主题,也就会有不同的构造。可说到底,沙石就是沙石,城市化不过是消解对未来的恐惧而做出的反应。
我倚靠着落日的余晖从坡上下来,橘黄色的工服和墙壁的颜色显得很相称。到便利店的路上要十分钟。狭窄的路边总停了一辆蓝色雪佛兰,没有见它开动过,也没有见它落了尘。每次经过那里都要把腋下的托特包夹到胸前,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往前几步路的酒吧刚亮灯,昨晚用剩的尊尼获加和孟买蓝宝石的空瓶子被店主放到门口供拾荒的老婆婆拾去。老婆婆到了门口,店主先是停下拖地的手,然后毕恭毕敬地说着“你好”“谢谢”“好声”这种算不上亲近的寒暄。
我躲在便利店门口的侧面,恰好不让红外线探测到我,慢慢挪动脚步直到恰好看到店长的身影,确认对方背对着我,我才进去。
“今天好早呀。”店里响起了迎宾的音乐,店长依旧是背对着我,把货架上的过期食品放在购物篮里。
“是的,可能日落比前一天早了几分钟了吧。”
“啊,也是过了夏至的日子了呢,今年的时间可真快过啊。”
把托特包和钥匙一类的随身东西放在置物间之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从后门出去,到了被铁皮遮挡住天空的半露天仓库,把店长的折叠床收起藏在纸箱子中间,清点起今天要上架的货物。
店长看上去是四十岁的妇女,长相也都是随处可见的类型,大鼻子,圆脸庞,因头发绑起来而露出的黯淡的额头,不过穿着工服的样子比外面的家庭主妇要少了几分土气。听上一任的同事说,店长是从另一个城市来的,离开了她的儿女、丈夫、公公来到这里的。她并没有选择回娘家,而是用早已凝固的表情来到这个城市谋生。我相信她与我一样,是被纯粹的潜意识带来这里的。她不一定非得和我一样热爱这里的电线杆。某些业已存在,尚未消亡甚至将会永存的事物将她留在原地。这或许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测,谁也不清楚那一副凝固、雷打不动的表情之下蕴含着什么。也有可能,我透过她那透明且坚实的外表所看到的是自己。毕竟我来这里不过五个星期。流传的事情有几分真我不清楚。同事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性,满嘴除了八卦就没有一件好事。店长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露出男人的哀伤。从那微垂的眼角中不难体会到她在家庭里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店长你和我呆在一起会不开心吗?”
“这话怎么说呀。”
“每次我一进来,你脸上的肌肉就会立马挤出微笑。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看错了,所以我就把那副景象尽可能地记录下来。在回家的路上不断学着你笑的样子。再过几次我才确认你的笑容的确是有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怎么说呢,可能是工作时需要的笑容。但哪怕没有客人你的笑容依旧是挂在脸上的。我会有些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和上一位同事一样把你放在一个尴尬的境况。”
“原来你是这样想。好开心啊,居然还有会有人在意我的表情。放心,我是真心地笑。你见过尸体吗?人在善终的时候就是会露出笑容的。只有麻木的时候嘴角才会下垂,我是从你身上感受到了放松的气氛。至于相似的境况,你就无需多虑了,你还没有男人的气概,顶多只能算是男孩。”店长在冰箱内的另一边换着货,用带有挑逗意味的好奇眼神盯着我。
男人的气概。店长说完这句话后,我用沉默作为这场对话的结尾。其实我明白男人的气概是什么样子的东西,非常清楚。那是和我自身一样,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令人生畏的存在。就在我准备沉溺进回忆的时候,外面进来了一位身穿棕褐色西装的客人,年纪约比店长小个几岁,他夹着公文包,像是监察官一样审视着店里的事物,然后无视我径直走向柜台,故作亲昵地靠在柜台上和店长搭着话。那位客人高度赞赏店长的劳动,纵使我无法否认店长的辛勤,但如此夸张的赞赏依旧过火。这段话很明显不是冲着“店长”的这一身份,而是“女人”的这一身份。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呼吸放轻。迈开脚步离开柜台对于现在来说究竟是否属于识趣的行为呢?我不敢实践,只好低着头默默地擦着柜台。离我右边半米的距离,店长露出了家庭中才能看到的隐忍的笑容,附和着对方的话语。不一会儿,两人就从后门出去,再稍等一会儿,就能听到那架折叠床摩擦震动发出的声音。
天花板挂着的电视正播着一场政治辩论赛,蓝色一方的青年曾经率领维和部队进入中东地区阻止本国军队的军事行动,红色一方则是本国现在掌权的领导者。二人就“建党自由”的话题进行争论。看着屏幕中两个男性脖子上声嘶力竭的血管,我很好奇他们的活力是在哪里来的。他们真的是人类吗?而不是被某个更高维度的精神体操纵的人偶?看到这几句话的人,你说我小人之心,那就小人之心吧。这种热情我从出生就没有体会过。
“啧,那种战争偶像怎么会有能力治理国家啊!不如把这些钱用在国防预算上!这个国家完蛋了……”那个男人胸前的两颗纽扣都还没扣上就狠狠踢在货架上,无视掉在地上的薯片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看来他的男子气概得到了释放啊。”
“原谅一下,他也只有在这些事情上有发言权啦。”
记于七月一日晚
七月二日 到七月六日 天气晴朗 微阴
这几天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没有晚霞,而且事情比较多。过去五天发生了什么也全然想不起来了。故到此为止。
记于七月六日晚上、七月七日凌晨两点
七月七日 天气阴
又做了那个梦,除了出门走走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消解睡眠给我带来的恐惧了。虽说选择这里作为我独游的中继点很大程度跟当地的静谧有关,只不过这份宁静在午夜是会有一些令人不安。我已经二十三岁了,也是过了需要PG家长指引的年纪了,于是我穿上便利店分发的薄外套出了门。
我租的房子在镇子的尽头,门口只有一条直达公路的路。酒吧离我这里不远,能在转角的路口处看到它的灯光。下午打扫卫生的酒吧老板在吧台上趴着睡觉,卡座上躺着几个见过一两面但从未说过话的居民。他们睡熟了,在大脑中凭借着自己的潜意识与困意角力。这是他们唯一剩下的力量了,倘若连这一独属夜晚的力量都得不到声张,那么他们便与死亡无异。被昼夜更替刷薄的眼睑,微张松弛的口腔,缓缓生长的胡须,生物的本性慢慢变成了城市的本性。A君可能是便利店的监察,B君可能是早晨的送奶工,C君可能是这一间酒吧的上一任接手者。可当他们躺下了,化作液体,他们都是一样的,就只是自己了。
一路打着无声的呵欠,泪痕从脸上一直泄到地面,在我身后留下漆黑似电线的黑色线条。头上飞过的鸟雀掠过的阴影令地面又暗了几分。我没有细致地比对泪痕与阴影之间谁更深邃,二者之间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显地展现在题干中了:飞鸟的阴影与月光一样都是作为半透明的媒介操纵着光影。而泪痕不是,它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面上,把空气中的尘土,疲倦,寂静具象化地笼络在一起紧贴在地面上,在未来的某一刻变成苔藓。
便利店不见店长的身影,我走进去,拿起一包大号的Haribo小熊软糖在机器过了一遍,往收银机里放了6.8块钱,把软糖朝着监视器晃了两晃离开了便利店。便利店门口正对着一条宽二十米的双向车道,两边都没有来车,于是我把软糖藏在衣服里,朝着对面的山坡跑去。
坡的顶端比便利店的招牌再高出一到两米左右,尽管如此,距离感让便利店再小了几分。便利店的品牌是连锁的,闪着黄和红色灯光的名字从楼顶伸了一半到屋体外面,斜四十五度角对着来往的车辆,就像美国乡村的路边餐厅的服务员在路旁招揽客人。
从坡顶往镇子里的方向看去,你会发现电线构成的形状像是某种蝙蝠形状的邪祟盘旋在城镇上空,又或是某种具有保护性的屏障。不论是哪种,其力量在明显的削弱,你从它的密度上就能看出。或许是疲倦了,又或许是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如今横亘在上空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作为某种人生的阶段。跨过马路,一旦进入到它的划出的领土,胸下六厘米的那个地方的跳动就会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电线把生物节律的误差调频到严谨的地步。可能我的笔触还不够纯熟,简单的比喻无法表达出我的经验。就让我用另一个不那么成熟、甚至有些出格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描述吧:
小明有一架用驴推动的石磨,已知驴一小时能转二十圈,每六圈能处理五千克的小麦。那么,在读这一题干时你想象出来的世界是以是什么视角的呢?你是小明?是驴?对你自己来说当然都是正确的,但客观来说,你是石磨。这是不可置疑的答案。也是我私人赏你的真理。至于为什么,那就请你这个幸运儿自己思索吧。
附近传来丧偶斑鸠的啼鸣,那哀愁婉转的语气与店长如出一辙。店长就是这么说话的,一开口,她那情人般的口吻吐露出来的皆是对自身生活的遗憾。咕咕的叹息佐证了她的无奈,独自一人睡在漏风的屋蓬底下则表明了她的觉悟。她是自然的,但绝非自由的。她通过不被所有人发现的隐忍独善其身。
至于丧偶的描述,请记住,这是一篇日记,一篇从一开始就打算展现给世人的日记。比起事实的真相,更应该注重笔者的想象。我不是史官,我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都想着尽可能少地承担来自过去的责任(不然为什么后悔是负面的情绪呢)。所以,我不打算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我们的世界大同小异不是吗?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
说到哪里了,不如就开始聊聊小熊软糖吧。
为什么我非得挑选Haribo的软糖呢?我需要一定的糖分来让我的大脑保持活力。我快打了两个小时的呵欠了,下巴和颧骨的螺丝都快松脱。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小熊软糖成了再好不过的润滑剂,它既能为大脑提供养分,又能将松弛的部分重新上紧。于我而言,它就是我机体的WD40。
待到我觉得无聊了,会把不同颜色小熊的各个部份咬下来,藏在嘴中,其余的部份直接吐在地上。然后用舌头把不同颜色的小熊软糖在口腔内拼凑在一起。可我从来没有张开嘴看过自己的成品,我只是享受着这一股复合的甜味,顺势找点事情做罢了。这大概也是我的天性之一。
下午四点,那时的阳光还是很强,天空是亢奋的白,歇斯底里地散发着热气和光芒。焦黑的斑鸠尸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我发现的。清晨的啼鸣就是因其而起的吧。鸟的脚和喙是绝缘的。这个知识是在很小的时候见到被电死的人之后才学会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鸟儿们是为了配合电线,才不断尝试变异出绝缘的双腿。鸟的尸体通体是同一种黑,像是在天空留下了一块鸟形的空缺,任何生物都能从那里进出。
我突然觉得无聊极了(或许是精力都被空洞吸走了),这世间好像没有任何事情我需要去看了,我对未知的向往也变得寡淡,一些能被当作动力的情感譬如:憎恨、渴求、恐惧、好奇,也在我的记忆中褪色。这是否该叫做麻木?在濒死之际我想我看到的不会是自己人生的闪回,或许是她的,或许是鸟儿的,总之我的人生就像是被半干不干的毛巾一样,再怎么拧都滴不出一滴水。我试图回想我见到的第一幅人类的尸体,它有没有像店长说的那样露出笑容呢?但就和我前面说到一样,那副黑色的人型空缺把我的记忆烧穿了个洞,一切明朗的细节都滑了进去。只留下虚线般的景色。
我用树枝把焦黑的尸体顶了下来。一只橘黄色,身体周围有白色花纹看起来像是破损的棉花公仔的野猫走了出来。先是用爪子轻轻碰了碰黑色的物件,又凑上前去闻了两口,然后像是叼起奶猫一样把尸体叼走了。
在这里——在落基山脉的西面,美加边境南面的一间小镇酒吧中——我要留下点什么。把这本日记用真空袋封装,贴在酒吧厕所水箱的盖子上,为了让别人发现,我现在正在把之前留下的荧光液刺破倒进水箱里,这样势必会有人发现水的颜色变了而来检修的。
记于七月七日夜晚十一点三十分
附录
这本日记最终会被他人发现,以免看得一头雾水,谨此记录我的梦(历史):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呢?首先是前情提要:我把暑期从一座农场挣得的五千美金交给和我年纪相仿的女性计程车司机,让她带我去随便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把钱花光就行了。站在现在的角度回想,她五官有些难以捉摸,好似她的记忆随着离别时的维多利亚皇冠消失在公路的尽头。如果各位要想幻想出一个女性的形象,那我就只能凭着感觉给你介绍一下对方了。头发将将及肩、寡言少语,眼神冷漠。行为举止以及给人的气氛能够看出她在少年时期所积累的完美无瑕的履历。成绩名列前茅,当过风纪、学生会会长,绝不在晚上十点后回家。家庭不算贫穷,甚至再多几个像她这样孩子也能负担,可她自由掌握的钱却仅能维持她的基本生活,一点冗余也拿不出手。她没有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将经济上的拘束怪罪到父母的失职。大学毕业后,再也没有受父母的接济,用奖学金租了一辆出租车的牌照,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人都见过,但在社会中绝对是少数的女生。
路程的起点是在西雅图东面一座叫Snoqualmie小镇里的伐木场旁边。完成了上一位顾客的行程后,她把车停在汽车旅馆里面,步行去了附近一家餐馆吃饭。我在伐木场恰好看见计程车那鲜明的黄色,径直朝它走了过去。我就站在车旁边,背着登山包一声不吭地看着车厢。我可能是古怪的,但大概没人觉得我会打破车窗把能拿的都拿走,那里不是那样办事的地方。等了半个小时,她左手提着一杯咖啡,右手托着一块放在纸盒里的樱桃派。于是我简短地说了我的需求,她简单看了我两眼就将我招呼上车。
我在后排落座,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连她将我送去哪里也不知道。女司机特有的沉默对我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特质。我们先是往南边走,一鼓作气开了两天,经过圣海伦斯火山附近的时候在那儿歇息了一下。由于圣海伦斯是活火山,所以用于防护火山灰的灰青色房顶到处都是,餐厅、警察局、住宅、仓库、就连死人住的坟墓上也有。电线也相比别的地方更加低垂。在镇子里绕了好几圈,都没找到有棚顶的免费停车场,只好加完油把车停在油站里面。这五千块钱虽说是车费,但就从发生过的事情总结,更像是旅游的经费,二人的食宿都会算在这笔钱上面。
我们彼此之间“谁先说话谁就输”的游戏,亦随着她的开口所宣告终结(如果你看过她的日记,她或许会说是我开的口)。
“你是不是认识电视上的那个人……”她抿了一口还冒着泡的热咖啡。
“法律讲明:‘亲属的事迹不能作为审讯的依据’。”
“他的事情算得上是英雄吧,而且我也没有在审讯。”
“那我就更不会说了。”
“我就当你回答我了。”
直到冬天,我看见她穿上家里带出来的美国陆军外套,我才明白为什么寡言的她要打探我的身世。我的哥哥和她家里人的立场是对立的。为了阻止中东的战事,哥哥带领维和部队与国家的军队对峙。结果在大众心中,国家的军队反而成了战犯,而哥哥则成了大众眼中的英雄。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好比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般(只不过没有浪漫的成分)处于敌对的阵营之中。
乘客和司机的身份把我们之间的嫌隙取替了,印象中还算是愉快的一段旅程。
皇冠的储物格里有几盒CD,Louis Armstrong的爵士、Beatles的摇滚、Minnie Riperton的R&B、松任古由实的流行。保守的、活跃的、乐于社交的、反叛的、充满恨意的、保有希望的,从她的音乐品味无法把握到她的性格。我最喜欢一盒从未见过的红色封面CD,里面第一首歌的名称叫:Wild West。
I’ve been living the edge of the life
Slip and fall if I take one more step
There’s safety in numbers, I guess.
But I’m going rogue in the wild, wild west.
第二首歌叫:I am
I’m a, I’m a, I’m a good man
I’m a, I’m a good man
B-back and forth
我们讨论过各自踏上旅程的原因,我着实不明白,像她那样的优等生为什么会开起计程车。“开计程车能当作毕生的事业吗?”
“我没有什么大志,甚至我觉得拥有大志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天赋。我只想每天找个没人的地方,买杯咖啡,吃个贝果,逗逗野猫,过年过节给自己买件新衬衫,待在车厢里听CD,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静待偶然的好事发生,这样的人生我已经足够了。”
电台的午夜报时结束后,我们决定把车停在路边找点乐子。沿着来时路的方向走五百米就到了刚刚看到的酒水店。她差三个月21岁,我差五个月,都不是能够喝酒的年纪。荧幕上,马蒂尔达问过我一个问题:是只有童年才这么苦,还是生活就这么苦。我的人生还没开始,我回答不了她,但我觉得如果有酒,事情一切都会好办很多。
我们甚至没有确认酒水店里是否有人、监控是否开着,这地方是不是折翼天使(摩托帮)的势力范围,冲进去拿起几罐蓝的红的就跑回车上,由得警报一直叫唤。我们大概偷了三瓶伏特加、两瓶金酒、一瓶龙舌兰、十一罐啤酒,跑的路上把龙舌兰摔破了,于是我们赶紧蹲下拿起破瓶子往对方嘴里把酒倒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那时候吸了点玻璃碎屑导致我现在的咽喉炎)跑回车里。
我们只喝了四瓶啤酒,半瓶金酒和两口伏特加,四肢就完全失去了我们的控制。我们硬撑着,交替掌握方向盘开了半小时,把车停在案发现场两公里外的岔路。
“还能走吗?”我已经记不清是谁问的了。
“不行了。酒驾很危险。”
“哈哈哈哈。”想不起来是谁笑的了,可能是我们俩吧。
“那就在这过一晚吧。把打开车门。”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熟,连她的梦话我都没有听到。但第二天,她和我说,她听见了我的梦话,我似乎在复述一件别人的事情。她只把其中的一部分告诉给我,但我立马知道是哪段记忆。
我离家的两年前父亲因尘肺病死了,死前的一个星期他在家里把我们都交过去各自交代了点事情。
“我还不能死……”父亲他喘了口气,重新发声,“我在等待,我在等待你找到一份事业,一份你真正热爱,真正能够将人生投入进去的事业。它不一定非得要富丽堂皇,甚至直到人生的尽头它都只会为你带来贫困哀伤。但你的事业会作为你生命的延续。相信我孩子,这是真的。有无数的人空有一腔热情,缺少对自身冷静的审视。遇见什么新鲜事就打得火热,青春消逝后只空有被烧红的空荡荡的躯干。有一句古谚语说得好:‘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努力又赔钱’。但我知道你会找到的,你和他们不同,我相信你会找到的。你会凭着这一事业成就你人生的延伸的。
“当你找到了,就不用再挂念我,届时我也安心地离世了。好好享受希望带给你的力量,相信你的眼神会变得锐利,穿过现世的重重迷雾直达未来,每一天都带着愿望过好每一天。”
这些话,是对哥哥说的。对我说了什么?那段记忆已经成为酒后早晨的第一泡尿,被我排出身体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是在黏润的泥土上醒来的,大脑的三叉神经像是灌了铅一样在大脑里左摇右晃,太阳穴都被里面的液体撞出个包来。我把座椅调低,从身后环抱她的身子将她拖到副驾驶的位置上,由我继续掌舵。沿着岔道,换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北向马路。开出半个小时后她醒了,用手检查自己的衣服还好好地穿在身上。
“我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
“不是在误会你。我闻不惯泥土的味道。你明白吗?就是那股青草被砍下头散发的气息。”她打开置物格,拿出薄薄的钞票在手里过了一遍,“没有多少钱了啊。靠边停下,让我来开吧。”
她每隔十秒就得打个哈欠,酒精在她嘴巴里沤臭的味道就算是在高速路上开了窗也散不去。我们买了一壶咖啡,一打糖霜甜甜圈,在餐厅简单漱了个口就继续上路了。我在一旁数着钱,算算除了油费还要腾出多少作为她的小费才合适。除了这一笔钱,我身上就掏不出任何一分钱,而且她几乎开车绕了华盛顿州一圈。分别最是痛苦,这句话还要再补个后半句:“分赃”尤其是。
当天,在美加国境以南,一个叫Everson的小镇再往西走几公里,太阳恰好沉入东边山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旅途的终点——一座早已被废弃的荧光液工厂。
她熟练地绕到厂房的后面,掀开被野兽撞坏的铁栅栏,爬了进去。荧光液的部分只是这片化工区的很小一部分,但在漫漫夜色中极为显眼,路牌、遗落下的荧光液、像是流动的霓虹光带一般指引着我们。厂房中间有一个水龙头,一扭开就会流出融在一起的荧光液,如果被基督徒看见,《圣经》又得多加一段故事了。
我问她手上那包气球哪里来的,她跟我说是那时候在酒水店抢劫时顺手藏了一包在衣服里面。她把气球的口撑开,灌满荧光液,半透明气球好似某种只在夜晚出现的生灵。她抓着被拉长的口子,用流星锤的方式甩了起来,狠狠摔倒天花板上。顿时整个空间亮了几分。接下来我们就反复进行着这个活动,把黑夜一点点染上属于我们的夜色。再到后来,我们几乎是玩起了躲避球,在五光十色的黑夜中相互朝对方砸去。她的手臂和下巴青一块紫一块,荧光色下也能稍稍看到被砸出的淤青。
“你这样好看多了。” 她的笑容像是刚被陌生人救下,被迫坦白自己轻生的念头一样,带有一丝羞愧的意味。
“你也是。”一开口,舌头也有微弱的光芒。
我们染上彼此的颜色之后,怎么也洗不掉,只好跑到棚顶休息。
写下我和她的经历的时候是带着担忧的,生怕她会被我的空虚浸染,在大家面前显露出的都是轻飘飘的形象。二人生活的真意要想用笔触写下,能传达的若是有三分那也算了,只怕当中连三分的乐趣都表达不出来,被旁人按照公序良俗的标准播下电话通缉我俩。诚然,二人生活的确会让公序良俗的教化减弱。我们一天能想出上千条不带重复的冒犯笑话,哪怕是极左翼的Yankees听见了都会不适。此外,两人旅行还有一个好处,对方的社交需求只能由你满足,也就是说,无论你说什么她都要听。在以前,别人和我说分“文”不改的同一句话,我都会觉得对方讲得更加有道理,更加有美学气息。这或许是奴隶的思想,人偶的思想。不过开始有人听我说话之后,现在我也开始觉得自己说得有些道理了。
“千禧年改变了什么呢?”我问。
“对啊,改变了什么呢?何况这世界本来也没有很好。”她把鞋子踢到下面的平台上,“马路变堵了,撞死在大楼的鸟多了,路边的假花也多了,大家都变得只爱倾吐自己的事情。我想就这些了吧,不过千禧年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掐指一算,如果我要有那时候的印象,那我得早出生六年。如果说是‘嗖’地一下的那种变化,我能想到的只有计数方式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都在往不那么可爱的方向发展呢。”
“Y2K把我们变成坏东西了啊。”
“所以嘛,有大志也不会变得更好。”她接着说,“那你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情吗?”
“嗯……打水漂。”
“打水漂?”
“想一连打出四十次。”
“有试过成功吗?”
“没有。尝试了八年也没有一次。我哥哥很厉害,学了十分钟就能打出四十一次。”
“我明白!就是那种要做成某些事宁愿把胃也要消化掉的努力,结果被别人随手一挥就办成了的感觉。”
“我以为你会是破坏别人努力的人呢。”
“是的,我就是。被批评了之后已经收敛很多了。学会怎么处理压力,是生活在天才身边的第一门必修课啊。”
“很寂寞啊,一起走了三四个月,把华盛顿州都走了个遍,结果发现我也不了解你。未来两三年如果还有机会碰面,我们大概只会点点头,当作陌生人吧。”
“我身上需要你知道的一切事物,在你见到我的第一面就已经全盘托出了。不过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碰面,我一定主动挑起话题。”
“真是反潮流啊。我得学学你才好。”
“Die Art und Weise, wie du eine Sache tust, ist die Art und Weise, wie du alles machst (How you do one thing is how you do everything) .”
终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915098f5-9f19-4d68-a4f1-4194e2ec4ff5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