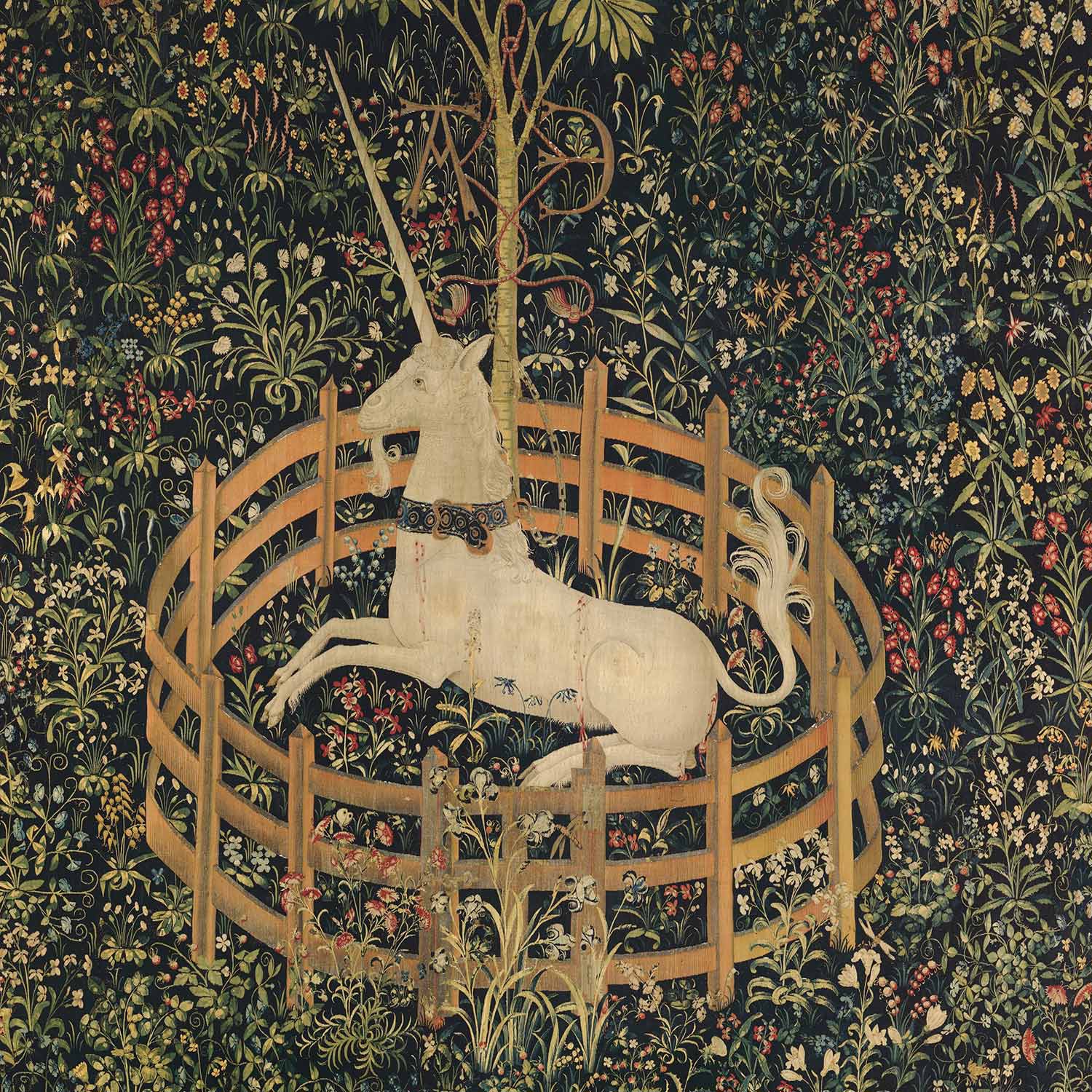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Apr 23, 2024
slug
summary
沉默的尖刺拥抱着我们
tags
文字
category
短篇小说
icon
password
明天就是和哥哥约定的探望母亲的日子。但哪怕我提前三天回来,心理上仍然没有做好回去的准备。
事发突然,从哥哥得知母亲失去意识的时候是半夜,我仍旧在私人的物流公司处理行政上的事务。大概是精神恍惚,我下意识地用了讨生计的敷衍语气应付了过去。我再想找补的时候电话对面只有重复的蜂鸣了。我担忧他过于疲惫,所以哪怕我一晚上没睡,也没有在半夜的时候向他报告回去的日期。半夜的我同样没有精力下决定,只好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
农村的午夜,天空少有地出现了洋红色,和母亲的眼睛一般微小的月亮直愣愣地在夜幕开了口子。明日的仓促、见到母亲的不安、和哥哥同住在一间屋子里的愧疚感,这些复合性的情感让我一整晚都睡不好。
我用酒店的电话拨通了哥哥的号码,等待时传出的低质量音乐令我更加恼火,我只好将电话稍稍拿开一些。
“喂?”电话那头传来声音,“喂?”
“喂。”
“是你啊。”
“是我。”
“这个电话是公司的吗?”
“啊,是的。”
“怎么用公司的电话打过来,打错了吗?”
“哪里的话。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了。就试着打给你。”
“是问妈妈的事情吧。”
……
“放心,她还挺好的,能吃点东西了。你明天能回来吧。”
“嗯。”
与哥哥的交谈比预想中要稍显轻松,或许是电话那头察觉到了我心里想着什么。总而言之,这场谈话将忧虑提起了几分,在心中显得不那么沉重了。
回到家后,各式各样的家具已经蒙上了薄薄的灰尘,而哥哥却还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坐在沙发。望见我后,指了指门边的房间。
房间出乎意料的干净,母亲就躺在床上,怔怔地望着天花板。
从母亲眼神的转变中很难体会出惊喜的情绪,更多的是遇见陌生人的好奇感。脸上疲于家事的皱纹终究是支撑不住,层层叠叠地显现出来,带有微妙的瘆人感。母亲的眼睑沉重地搭着,却毫不含糊地暴露了对我的陌生、不信任。她没说什么,轻轻瞟了我一眼就闭上眼睛睡了。
母亲一直都是率真的人。在失去父亲之后她的率真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发扬。母亲在十八岁的时候生下了哥哥,二十六岁的时候生下了我。好在出生得早,我出生十一年之后就是计划生育。母亲在文革时插队到了西藏,父亲去了武汉。回来后母亲当上了小学老师,而父亲就在镇上的水电厂做电工和会计。父母离家的那段时间我就和哥哥一起在爷爷家生活。但以前发生了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很吵,很闹,记忆就被这些喧闹隔绝了。
母亲的率真在家里不时会演化成冲突,二人吵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亲戚。父亲总不想接济他那因生产事故而少了一根手臂的弟弟。母亲却经常搬出“长兄为父”的言论,无论如何也得礼貌性帮补一下。父亲说过最伤人的话就是“女人懂什么,别插手我们的家事”。听了这句话的母亲狠下心来就跟他打了起来。当时村里还流传着一个谣言,父亲在武汉插队时认识了一个新的女人。母亲表面上不在意,可说多了,也总会产生自我怀疑。父母之间就这么绷着一根暧昧的弦,我们每次走过都会被绊倒。
事情的转折点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夕,母亲因为跟合作社的人吵了几句。某天晚上趁着父亲下班,对方带着人把他狠狠打了一顿。余下的日子他就只能在床上生活。父亲听见母亲安排家庭事务的时候,默契地什么也不说,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外人”一样。久而久之,母亲的工资和我们帮忙养鸡的钱已经不够负担起医药费。只能让两兄弟的我们一个出去城里,另一个呆在家里照顾父亲。
我们用了土办法——抽签。因此最后也是我出去了。
再过了几年,父亲死的时候,门前有很多人来吊唁。我很惊讶,父亲居然在镇子上有不少威望,和母亲嘴里的样子完全不同。来的人我大多没有见过,要么戴着军帽,要么西装革履,热情款款地和哥哥以及母亲寒暄。轮到我时就简单地握了握手。那位失去了手臂的叔叔也来了,以微妙的表情望着含糊不清的遗照。我对这光景或许是稍显冷漠了些,面无表情地四处张望,以至于他们上前时都不清楚该以什么样的神情对我。我也拥有同样的困扰,习惯了城市的孤独在礼教方面不及他们,我也只能不合时宜地嘴角上翘。
处理宾客的帛金的时候,我发现流言中父亲的情妇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红包满满当当的,不像是只有钱在里面。我趁着母亲不注意,将那个名字删去,将红包原封不动地藏在箱子里。我思来想去,检索不出那个神秘的女人的样子。
半夜,我和妈妈单独坐在厅房。我这才想起,原来我几乎没有单独跟母亲说过话。每次都因巧妙的琐事将我们隔开。就好似住在隔壁舱房的两个囚徒一样。
我对着母亲冷静的眼神说,“以后怎么办。”
“既然出去了,还是留在外面好吧。”
“我明白了。我会多些回来的。”
“这些漂亮话就不用说了。女人的寿命总会比男人长的。所以我也做好了一个人的心理准备。”这些话,是母亲独自对我说的。好像用了更辛辣的话语盖过了父亲死亡的哀伤,心里酥酥麻麻,品不出什么。
门外的天井黑漆漆的,只能依稀辨认出田鼠的轮廓。我小时候一闹腾,母亲就会把我关在门外,让我在看不见星星的夜晚忍受着黑暗。我的哭闹声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好似固塞的黑夜径直立在门前,不让我的声音传到里面一样。所有的不安、外界的虚伪被我的嚎叫吸引过来,为我穿上了带刺的贞操裤。每一次到了最后,都是父亲忍受不住,将我接了回去,父子二人默默受着母亲的责骂。
“你还没睡呢。”我对着坐在沙发的哥哥说。
“没有。怕老人家半夜想要上厕所。在房间里容易听不到平安钟。上次就是睡着了,结果妈直接尿在床上。老人家也是要面子的。”
“辛苦你了。”
“我儿子还没回来吗?”
“这个点数,大概在机场了吧。”
“从美国回来的机票不便宜吧。”
“还好,目前是淡季,也就八千块。”
“八千啊。”我看见哥哥的手指在算着什么。
回到房间,午夜的湿气渐渐重了起来。单薄的墙壁透过了几声母亲沉重的喘息。我犹豫是否该替侄子铺被子,还是让这个责任交给哥哥。可一旦让他代劳,势必会引起我们之间不愉快的回忆,无疑会让我在家里的日子更加难过。担忧之间,身体便不自觉地将被子整理好了。
侄子那不长的人生大多是和我一起生活。为了上学,哥哥把他送来我家。而我将他从哥哥找的学校转了出去,到了市重点学校的国际班里。新学校允许走读,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东西方的节假日,偶尔也不时会举办家长日。这让无法生育的我来说算得上是一种慰藉。
妻子对这件事并不抵触,她也明白我有多想要一个孩子。不过她对侄子与哥哥父子关系的疏远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哪怕我不愿意,也会定时带他回去见一下哥哥。
“这孩子这样下去不行吧。”妻子说。
“已经到年纪独立了,出国留学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说。
“我不是说这个。那毕竟是你哥的孩子,还是得说一下吧。”
“没有这个必要了。能出去留学他应该没有反驳的心思。”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哥的另一个孩子患了肺病去世了。他把更小的孩子放在我们这儿本来是担心传染,结果你倒好,自顾自地把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你也想想家里人是怎么想的吧。被迫无奈让孩子寄人篱下,他怎么可能乐意。”
“我知道,但这是他的选择,我不过是尽自己本分给他提供最好的。不过,上次打了那孩子,我真是有些后悔。他是不是记恨我了。”
“你也知道啊。姑且不论孩子怎么想,那毕竟是你哥哥的孩子,于情于理也都不该动手。”
“但他的学习不让人省心啊。”
“最不让人省心的还是你。”
“话说回来。那孩子不知道自己有个哥哥吧。”
“不知道。还小呢。”
“唉。他也从来没问过自己的母亲是怎么死的。”
“还不都是你把他接了过来。我也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一个孩子。”
“可能是我精子有问题。所以我才想着要拼了命地要一个孩子。话说回来,这些年也真是辛苦你了,其实你很不喜欢小孩的吧。”
“是不喜欢。不过也算了,他毕竟也不是我们的孩子。”
“婚检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很高兴吧。”
“我不喜欢你说这样的话,好像什么都得要算计一样。时时刻刻都想着要人欠你什么。就算你能生孩子也不见得我就会离开你。这不都是婚检才知道的事情吗。我没图过你什么。”妻子悻悻地转过身子去,只给我留下背面。
“已经半夜两点了,快睡吧。哥哥那边我会说清楚的。”
当然,还没来得及说,事情便被哥哥发现了。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愤怒,为了不输给他,我用比他还要大的声音反驳。被我这么一吓,他好像做错事情的父亲般缩了下去。我不是没有愧疚,只是不能在孩子面前弱下去。
母亲不久后死了,侄子刚好见了最后一面。令我很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过来吊唁。我原以为,这些年我为村里捐的钱能够让他们过来,撑撑场面。哪怕是不为了母亲,也该是为了我。心里有种寂寞漫延上来,不是因为母亲的死,而是没有达成目的的遗憾。有些叫不上名字的人见我哭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节哀顺变。
直到最后,我也没看见那断了臂的叔叔。宾客散了,我忽觉这座房子很安静,就连放的哀乐也觉得比以往小声了。我甚至扭了扭音响,确保声音是最大的。
哥哥还是一如既往地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我不忍心让侄子刚调整好的时区再一次紊乱,便由我和哥哥为母亲守灵。母亲的照片只能找到我小时候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拍的,中间几十年我们也拍过一两张照片,但都没有笑容。母亲青春的面容和冰棺中惆怅的皱纹之间有着明显地隔阂。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呢?
“听村里人说,好像你身边的女人不少啊。”我对哥哥说。“嫂子死了这么久,也是时候找一个了吧”
“他们乱说罢了,我没有那个心思。”
“以后,不如也和我出去吧。留在这里也没有意思。”
“别忘了,我比你大八岁,几乎算得上是两种时代的人。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寂寞吗?说句不好听的,以后我回来的日子只会更少。”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这句话和父亲去世时母亲说的一模一样。好似他们二人独立于我之外有着某种联系。
“我老了。如果你想当大家长就给你当吧。你没有孩子,就把我的儿子拿去吧。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好好静静。”他的语气中充满着受害者的无奈。
哥哥站起来,走到母亲的房间里面,翻找着什么。不一会儿,他头上的白布已经摘了下来,手里提着一个掉漆的木箱子。径直朝着外面走去。
“妈什么也没留给我吗?”我把他叫住。
“自己去找找吧。找不到的话就是没有了。”
“那你能帮我找找爸治病的钱吗?”
他气愤地摔了手里的木盒,掉出一叠五元十元的零钞。“对,我是拿了爸治病的钱,那又怎么样。他已经插着管了,还能怎么样呢?你认为他这么继续活个一两年很光荣吗?他不希望有人来看他你明白吗?你要当你的大家长是你的事,别冠冕堂皇地说为了他好,为了他好。是他让你出去的,是他让我把签给掰断把机会让给你。我不介意生活被夺走,我不是要报复,也不是要补偿,更加不是要把这些事情怪到家人头上。一个人要做好人坏人是自己选的。我只不过是想要治好我的老婆,这有什么错!
“这是我的钱,是我妈留给我的钱。爸他偏爱你,把一切都给你了,妈留下的总归是我的了吧。”不知为何“我妈”这两个字好像有些刺耳,像是捅破了我的耳膜一样,只能听见无序的蜂鸣。
“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这盒子就给你算了,你要什么就全都拿去吧!”
在那盒子里,除了存折和零钞,还有一张出生证明。上面的名字有我、有父亲,还有一个传闻中父亲的情妇的名字。
事到如今,我也不清楚,这个出生证明是不是母亲故意放在那,作为对我的报复。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866c4ee3-cec6-4e53-b457-3dfe5f41e3bf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