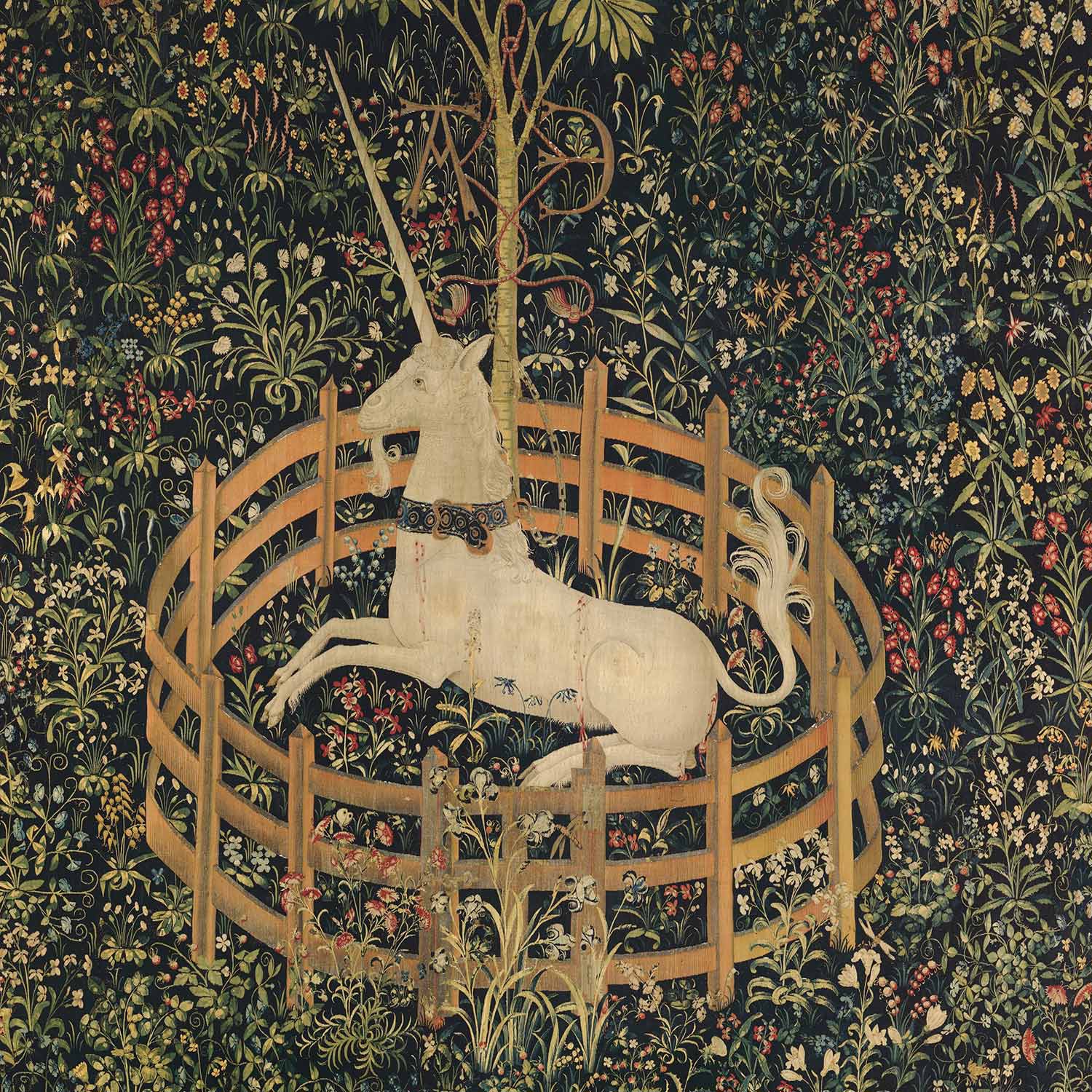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Dec 29, 2024
slug
summary
tags
文字
思考
周记
category
学习记录
icon
password
周一
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人。
当时签证机器坏了,只能去出入境大厅里面办。当时还是疫情,出入管制依旧是常态,更不要说在机关单位了。门口有个大叔,穿着一眼就是“半个警察”的样子,来放行门前排队的人进去。里面有个穿着蓝色外套,看上去一眼就是机关人员的样子,戴着眼镜,看着很斯文。每次进去的人数都不一定,偶尔七人,偶尔八人,每一批的间隔也不同。我恰好是队伍的最后一个,跟着前面的两位女士后面一起进去。但就在我排队到一半,约莫十五分钟,后面又进来两三批人的时候,那个大叔就走进来,对我说:你干嘛偷偷跑进来,没看到要排队吗?我也顾不上周遭的环境跟他大声地争论起来,他没有反驳什么,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回去门口站着了。我看到戴眼镜的那位男人跟他聊了点事情。我就明白大概是里面太挤,把大叔说了一顿。这件事背后大概是没人受到处罚的,除了我受了点不明不白的冤屈之外。
后来细心一想,大概是他在公职机关作为非公职人员,没有相应的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才会说我一顿,以便将责任转介到我的身上。毕竟我被说两句对我并没有实质上的伤害,但他如果没有说我这两句,可能就要遭受实质的伤害。社会的责任在这时就被实体化了。它可以依附在金钱、职务这类能够摸得着看得到的方式,以“物”作为标的展示出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认同这一个“物”的价值,为了保存这个价值,他们便会对“责任”进行处理。
我们先来捋清楚社会中的责任具有哪些层级,很明显,上面的例子中,大叔对我进行批评是合乎效益的,在处理“管理人员流动失误”这一项责任上他将一部分责任转移到我身上,从而令自己所受的“物质代价”更微弱。在这里,我们就能至少对两种责任分出个等级:在他眼中,情绪代价要比物质代价更加低廉。用这个道理代入回去就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伤害了我的感情。
责任是社会的一部分,而社会又是人类世界观的重要组成,即现实的一部分。大叔没有选择直接承担这个责任,而是将我作为媒介增加责任传递的环节。就跟科学中的能量转移一样,将一部分能量传递到我的身上,紧接着我只能通过我自身的反应将这个能量消解出去。跟所有的化学反应一样,一切传递过程都会对力量进行损耗,在无形中对整个社会进行影响。我愿称其为:“社会版的熵增定律”:现实的总和只会增加,不会衰减,责任的转介并不会削弱现实,甚至不会削弱事件带来的后果。事实上,我把这件事写出来,就已经是“责任”的后果,我的思想因为这件事而起,然后我将它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无形中为社会增加了能量。或者另一个方式,我被冤枉之后感到委屈很不开心,我选择花钱来消解我的寂寞,金钱流动到金融体系之中带动社会经济运转,同样也是责任的后果,只不过花钱这一方式更加直观。
开解自己的方式大多都需要成本,当责任开始不断地流转,到达许许多多无关人士身上,能量就会在他们身体中积压,责任传递所损耗的能量也会令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变好变差不一定),等到某一刻发生触发点,就会燃爆个体的精神,为了释放自己的能量而无法控制自己,做出种种极端事件。那么这一责任的传递就会几何级的增加,导致社会的能量进一步膨胀。
有点感冒,就先写到这里。希望各位都能尽可能与人为善。令正能量与负能量对冲一些。
周二
夏目漱石在《文学论》提出这么一个公式:F+f,其中F代表焦点印象或观念,f则表示与F相伴随的情绪。这是用来描述文学作品当中的基本要素,是文字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的基本材料。我们没有必要弄清楚每个字母代表着什么,只需知道它的大致意思就好。因为每个作者的文体都不相同,F当中所填充的意义也不相同。伍迪·艾伦热衷于使用大量的“废话”作为文体的主要构成成分,可以说,他的F是人物对现实的见解(作者本人的见解被隐藏在其笔下的所有人中),这一见解同时也能作为推动故事的发生。而像《活着》、《丰乳肥臀》、《黑暗地母的礼物》则是注重于作家本人所构建的现实,是基于客观世界为舞台而进行稍许文艺化处理的方式。两种叙事方式当中的F是截然不同的。
我个人写小说最重视的是角色间的对话。甚至我可以像日本流行的“电话小说”一样纯粹靠对话来写一系列小说。我最初接触到这一形式是在香港小说《玛嘉烈与大卫的苍蝇》。这本小说全篇只有主角二人的对话,剧情很难称得上有,只是借着情侣睡前的绵绵细语勾勒出冷漠现实中的浪漫爱情观。
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要求:有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不光是打破第四面墙对着观众说提问,而是在故事的编排、思维碰撞的方式甚至是文字的排版上都下功夫,在尽可能让读者明白故事发展的同时留下隐晦的线索让故事具有“连续性”。对话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互动方式也能基于此发展出各种不一样的延伸。就跟我前面所说,对话除了有推动剧情的作用也有把作者自己隐藏起来的效用。在读者阅读我对话的同时去推测我本人的想法,我很着迷这种与读者博弈的感觉。另外,对话也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有些事情不说出来,是不会相互理解的”。我对城市中的“纵深感”十分着迷,举个具体的例子:香港以及广州有不少巨型的住宅,有的还能被叫做“怪兽大厦”,一想到人们被这种城市化产物所连接在一起我就十分着迷。而城市化同样也带来人际关系的淡漠,在意识形态上的连接变得越来越淡薄,就连对话也变得无趣起来,我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将不同角色以及不同阶层甚至是不同世代所连接在一起。我想可以进一步作实体化的比喻,我好比是一个土木老哥,从零建造起属于我的“怪物大厦”,个人思想哲学是作为承重柱勾勒出大致的境况,而对话则是承重柱所延展出来的墙壁、横梁,故事架构是作为大楼的主体,角色则是令大楼变得吸引人的外貌。在这一比喻中,我想借用日语中的“物语”会更加恰当,小说作为“虚构的物语”是“真实的物”本身借由文字的表达,背后是有作者本人对“真实的物”的看法。我不怕得罪人地说,在中国作家上,我只能看见“物”,看不见“物的表达”。
我对对话有一个要求,传达的对象必须要尽可能少。二人聊天的场景如果只有两个人就最好,倘若被迫有第三者插入,那么第三者也要尽可能不说话,直到话题过去了再进行参与。对话只有在两个人之间才足够坦诚。倘若三个人都是话痨,不光对读者也是一种压力,对作者来说也很难把握当中机巧,三个人说起话来客套话和废话就必须要几何级地多起来。就算是夏目漱石,他在《我是猫》中描绘的知识分子对话也令我厌烦。一是废话太多,而是大家说的话大同小异,纵使将当时的社会风采展现得恰到好处,我也无法接受。其次,对话一定要干练,说出来的话要尽可能短,但又不能像海明威那样将70%乃至90%的内容藏起来,势必要精准无误地表现出角色或是自己本人想要的主旨。鲁迅在《阿Q正传》的开头、芥川龙之介在《父》的结尾在这一点上可谓是鬼斧神工。
当然也有可能,我爱写对话是因为我平常不说话,才对对话有这种追求。
周三
我凭直觉抽了两本挤压已久的书出来看,我的习惯是一本电子,一本实体,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转换传播媒介的方式让自己的眼睛休息一下。说来也怪,只要是我凭直觉的抽出来的书(我事前对内容没有任何了解),当中都有相当强的关联性。一本叫做《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另一本叫做《連結——从石器时代到AI纪元》(据说简体被删了几十页,我没有求证,图方便就买了繁体版)。目前来说我都没有看完,但它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问题:咨询并不是为了呈现事实,而是为了笼络人心。用《〇〇年代》的话来说就是:叙事的真实性来自意识形态,而面对叙事的态度则决定了能否通往交流。《〇〇年代》是一本着重研究00年代日本亚文化的社科书籍,而《連結》则是剖析从古至今的文化团体是通过什么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一本是具有流行性的书,一本是跨越时间具有普世意义的书。两者似乎都在谈论这一件事。倘若这背后的事物具有“流行性”,那么它就没有“普世意义”。这种矛盾我想必须要在我看完这两本书后逐渐弄明白“背后的事物”是什么才有意义。
但我们提到:叙事的真实性来自意识形态。结合其流行性,我很难不联想到外面的华人圈子中有一位发行了“memes”电子货币的超量级政治网红Lee某人。他具体是干嘛的说出来会引火上身,只能大致介绍一下。他喜欢收集东方某国的“负面咨询”整合后发到网上。并标榜自己是“新闻人”。而实际上,有的人也能看见他的评论区下面有许多辟谣的评论,不乏将过去的新闻当作是现在发生,或者是将事件张冠李戴,扭曲行为本身的意义。这个账号却具有三百万的粉丝。这恰巧跟“叙事的真实性来自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谋而合。
任何的意识形态都不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同样,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中特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史观”都无法还原,甚至它们其本身就说明了历史是构建出来的,是为了笼络人心所构造的。“历史应该为民族(国家)负责”这同样能在各个红色阵营国家中听到相同的话。那位网红的事情就聊到这里,如果大家不幸刷到,我希望各位能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咨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咨询能多大程度还原真实?这个咨询有多少部分是可信的?
回到这两本书,我认为“背后的事物”同时在“流行性”和“普世性”的冲突可以归为作者本人的局限性。写下《连结》这本书的人自己同样是“流行的”,他同样无法脱离自己时代的偏见,也只能按照“流行”的观点去解读历史。历史的解读是具有滞后性、时效性的。我们要分析一件事、一个人只能完结之后才能去分析,才不至于是片面的。好比B站弹幕对希特勒的评价,从十恶不赦的独裁者转移到:孤身一人对抗世界,最后在地堡和妻子自杀的英雄。这种转移是从“反战”到“反犹”的价值观的转变。
中国互联网和日本互联网不同,日本社会缺少一个能够连结全体日本国民的“文化主体”,而中国则相反,我们的文化主体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切文化都要在它之下进行审核,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在它的土壤生长。我们可以将它比作枝干,其它的亚文化则是在这个枝干上延伸出来的枝叶。基于这一枝干延伸出来的亚文化和“去中心化”(即不在它的庇荫下发展)的亚文化是互不融合的,甚至是互斥的。官媒热衷于捕捉互联网热点,然后嫁接到自己的“枝干”上,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笼络原本亚文化的受众,而是服务原本就生活在其荫蔽下的群众。将原本就带有“街头”、“反建制”、“反叛”的事物笼络进主流叙事只会是适得其反。现实究竟是真实的繁荣或是亢奋的腐坏,还是得等时间陈化。
全球在政治上都在经历着一个右转的风潮,地方保护主义、民族保护主义、反贸易全球化,越来越盛行。但是在社会中,“不信任政治”、“不信任社会”、“不信任成年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既然选择什么样的叙事都没有区别,不如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物就好了。”这冲突背后的事物是什么我也还得继续观测。
不过在互联网这种“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咨询”的平台,要想把握去全貌还是得慢慢研究。
周四
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品应该是《新世纪福音战士》没错了,当中有许多元素都被我参考进我的长篇小说里面。现在开始分析自己写过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受其影响或者说受到背后相似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要更加深刻。换句话说,我是在相似的社会环境底下借用了庵野秀明的方式构建我本人脑中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的参考。
碇真嗣是根据父亲的命令来驾驶机器人战斗,而在父亲背后则是某种宗教性存在的驱使。出于对父亲的不信任,而拒绝战斗,因为这种抗拒的心理才导致后面接连发生对碇真嗣冲击的事件。最终选择封闭内心,什么也不做。转身投入到女性的怀抱,借由女性去为他开解。结果与其相反的则是《高达Seed》里面的基拉大和,他在自我封闭的过程种则是靠芙蕾和舰长所启蒙,在战争背景下找到自己的路。但基拉大和并不是跟碇真嗣一样,直接与世界兴荣所联系,而是作为军人、调整者等等身份为媒介参与到世界的运转之中。这种区别在我的长篇小说中也有体现,柏妍一开始也是直接受到某种类似神谕的启发,才决定要开展自己的行动,父亲和超自然力量的位置是与《新世纪福音战士》恰恰相反的。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她并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行为,她怀疑过这一行为是否是必要的,但对于最终目的她并没有动摇。
我必须不大得体地这么说一句,我写这篇长篇小说时,并没有这么细致的考量。我对写作是:不想写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是基于这么一种依靠“自然本能”、“灵感”的驱使。可能无形中我也是对自己的潜意识中《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一种回应。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还未从自己心中的阴霾走出来。几乎是被害妄想地对社会和世界不信任,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家门口都畏惧走出,畏惧去做任何事情,畏惧去迈出自己的一步。我在设计为柏妍设计使命的时候或许也是在为自己设计一个使命。我作为00年出生的龙婴儿,我自认为在身体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甚至这种使命感是超然于任何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乃至朝鲜这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也出现了00年的反叛潮流。这种带有流行性的文化观我也十分着迷,日后再来细说。回到原来的话题,我可以说是被庵野秀明那一句:“被选中的孩子出生在00年”所点燃,才有想要做些什么的冲动。在此之前,我写短篇小说的周期不超过半个月,这种行为就像是自渎一样,不断地通过释放自己去寻找意义。而写出来的文字也跟淡薄的精液一样,没有我的一部分,也没有逻辑,更没有故事性,只是为了写而写。所以我才有意识地想要拉长我的周期,直面这个社会的叙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因此我才开始想要写长篇小说来慰藉自己,告诉自己或许自己有写作的才能。
虽然周记主要的部分已经写完了,但我友情提醒一下,如果各位不想看这么长的周记,可以直接看每一天的最后一句,我一般都会做个总结。今天的总结不是为了表明自己多么“精日”我只是很好奇日本流行文化背后究竟有什么这么吸引我,因此我才去试着弄明白。我在写作功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平常也要有意识地将周记的文体调教得精细些。
得先明白自己,才能明白自己要写什么。我争取从写作上“本能”,转移到“叙事”上构建。
- 作者:dororo有几何
- 链接:https://dororodoujo.com/article/16ca3021-e025-806a-b5ae-d9e6e3acc0d0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




.jpg?table=block&id=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t=716d9b31-3f25-4834-afe6-5af102805eed&width=1080&cache=v2)